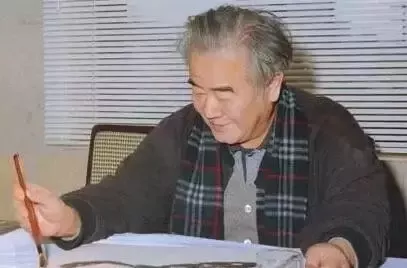|
套用一句时下的流行语,黄胄对于当代中国美术史是一个“现象级”的存在。20世纪中国画在人物画的发展上有着重要的突破,黄胄“在生活中起草稿”,以速写入画,以迥然不群的面貌崛起于上世纪50年代,成为徐蒋之后,中国当代人物画发展的又一里程碑。在其后,传统笔墨与素描造型的融合逐渐找到了感觉,黄胄以自己的天才和苦修开启并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艺术思潮和审美风尚。 评价任何一个人物都必须还原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黄胄生于1925年,卒于1997年,历经了中国上个世纪的几乎所有的战争、变革与转型。72岁的寿龄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并不算高,尤其对于先凭生活颖悟,后始苦修传统的黄胄而言,确实太短。如果把那段历史拉的足够长,以一个后人的目光来阅读黄胄先生艺术之路上的种种细节,其实,成就与缺憾,幸福与苦难,荣耀和流言,黄胄先生的幸与不幸都是时代所赐。
1957年作 小哈萨克 幸遇韩乐然与赵望云 尽管黄胄在遇到韩乐然之前,就有了一些美术功底,但与韩乐然的相遇让黄胄真正找到了踏入艺术灵境的法门。韩乐然(1898~1947),朝鲜族人,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巴黎卢弗尔艺术学院有过系统的学习经历。他认识黄胄时,正在西安举办个人画展,并准备到八百里秦川写生。作为助手,黄胄在韩乐然这儿获得了他需要的一切,包括素描、敷色、形体的准确与绘画的布局,随后,他又跟随韩由宝鸡到华山,再到八百里秦川的旅行写生。这段经历对于黄胄而言弥足珍贵,他不仅学到了写生的技巧,而且也感受了韩乐然在水彩画上用水用色酣畅淋漓的气势,这种气势后来被他成功得转化到他的笔墨中。
40年代的黄胄 黄胄后来多次提到与韩乐然同处的这段情谊。回头来看,黄胄幸遇韩乐然,在恰当的年龄完成了艺术技巧的启蒙,韩乐然也幸遇黄胄,尽管后来英年早逝,但“黄韩之交”在美术史上也留下了一段佳话。 赵望云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黄胄父爱缺失的遗憾。遇到赵望云时,黄胄刚19岁,放到现在还只是一个半大孩子,所以,赵望云对黄胄的影响不仅仅是体现在术上,还包括人格、秉性、价值观等各个方面。与黄胄情同父子的赵望云1949年5月送他参军,直接影响了黄胄的人生道路和艺术道路。黄胄的成名作《苹果花开的时候》与《打马球》就取材于随后的军旅生活。
1972年作 幸福一代 如果说黄胄幸遇韩乐然完成了艺术上的启蒙,那么在得到赵望云的悉心教导之后就深入了艺术的堂奥了。在参军之前,黄胄还做了外两件事情,一是赴河南开封《民报》工作,并赴黄泛区写生,后来这些写生作品陆续发表,为黄胄带来了最初的名声;另外一件是负责编辑《雍华》,得以结识徐悲鸿、叶浅予、张大千、黄苗子、丁聪、吴作人、黎雄才、俞剑华等人,并在稿件来往中得到艺术的交流和滋养。
1962年作 巡逻图 1942年赵望云定居西安,在中国美术史上是一件大事,直接的效应就是开启了“长安画派”的形成。赵望云所倡导的农村写生,也被黄胄接过衣钵,并以写生做武器,“在生活中起草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主张。“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赵望云对黄胄的艺术发展有多重要?如果说黄胄是中国当代美术史的一个“现象级”存在,那是因为他站在了赵望云的肩膀上。
1964年作 洪荒雪原 欣逢新时代 黄胄的老朋友宫达非在《生活•社会•时代—评黄胄之画》一文中记述:“1964年毛泽东主席与友人谈及中国百年画史,从“扬州八怪”谈到齐白石、徐悲鸿等大师时,曾这样提到,黄胄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有为青年画家,他能画我们的人民。”
1982年作 民族大团结 在1949年5月参军之前,黄泛区写生是黄胄最重要的作品。《小乞儿》《家住水晶宫》《行行好吧大娘》《孩子快死了》《草根养活的娘们俩》《黑热病患者》等一系列悲天悯人的作品,刻画了黄泛区难民贫寒交加的群像,始终贯穿着画家“哀民生之多艰”的悲愤情怀。黄胄在随后《雍华》第8期《画家与时代》(笔名梁叶子)中说道:要做一个新时代的画家,只是会追求与开辟自己的美的艺术领域,只是自己吃饱了饭便忘了那些没有吃饱饭的同胞,是不够的,他是应当和别的艺术一样,永远站在时代的前端,不是同样的可以作为时代的号角与黎明的晓钟吗。”尽管这组作品笔墨风格略显稚气,还脱不出其师赵望云巢穴,但其中的悲悯情怀,其中的历史担当,足以让人动容。如果历史再拉的足够长,相信这还会是黄胄最重要的作品。
1975年作 风华正茂 黄泛区写生的作品主题和气氛显然受到了蒋兆和的影响,在其中也看到珂勒惠支的影子。这种主题和气氛的作品,在黄胄其后的作品中少有延续,这显然是受了新时代的影响。1950年的《爹去打老蒋》或者可以算两种风格之间的过渡,尽管也属于新时代的主题作品,作品中的随意和放松已经显示出画家的格局气度,这也让徐悲鸿注意到了黄胄,徐先生的早逝没能让这种知遇沉淀地更加深厚,但足以让黄胄从此全国知名。我们不知道,在两种格调之间的转化黄胄用了多长时间,克服了哪些困难,但从1952年《苹果花开的时候》开始,黄胄的创作开始进入了新时代,《打马球》、《庆丰收》、《载歌行》,一直到前期最重要的作品《洪荒风雪》,作品充满了激情、豪迈、欢乐和清新,中国当代人物画史上的“黄胄影响”来了。
1962年作 高原子弟兵 尽管60年代末不可避免的受到文革的冲击,等1972年黄胄重拾画笔的时候,这种激情显然没有被冲断,后期的《姑娘追》和《叼羊图》显示了老黄胄一如既往的激情,一如既往雷霆万钧气势撼人。在激情当中,也有《育羔图》《塔吉克女教师》所流露的恬淡、安详与从容,显示出老黄胄在风波过后“也有风雨也无晴”波澜不惊的心态。值得一提的,或者还有1976年的《曹雪芹》,此年初黄胄移居北京西郊黄叶村(传闻曾经是落魄曹雪芹披删十载《红楼梦》之所在),或者此时的心情暗合,图中曹沾双眉紧锁眼神锐利,气氛凝重,令人为之郁结心动,此作再现了黄胄在激情欢快之外的情绪渲染与营造能力,与当年黄泛区写生作品的悲天悯人呼应,但可惜此类作品很快也淹没在新时代的欢快中。
1975年作 春风拂柳运粮图 一个时代会成就一个大家,新时代的黄胄是各种因素所造就的。“在生活中起草稿”,军旅的生活造就了黄胄的激情豪迈,新疆的风情也适合清新欢快的调子。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体现黄胄的另一面的悲悯胸怀和历史沉重被淹没,可有识者认为此也是黄胄之失?欣逢新时代,成就了黄胄也偏颇了黄胄,幸欤不幸? 著名画家冯远如此评论时代的黄胄,“我们既然承认,是时代造就了黄胄,时代也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黄胄,我们就无法苛求某一个画家在他生命的每一个时段中都要表现出超常的智慧和能力,始终扮演弄潮儿的角色。每一个个体的艺术家只要能够相对圆满地解决好一两个他所处时代的重要课题,便是了不起的贡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术史中的黄胄对发展当代中国人物画的贡献就很值得我们加以肯定和敬重。”此诚为持中之论。
1972年作 出诊图 写生与速写:我自用我法 前三百年石涛,后三百年黄胄。与石涛在写生的态度上一脉相承,黄胄对石涛的“搜尽奇峰打草稿”“笔墨当随时代”心有戚戚焉。与其类似,黄胄也有自己的主张“在生活中起草稿”。黄胃曾有世无英雄之叹,“石涛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有一得之见,三百年来竟无人突破”。黄胃始终坚信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他认为大画家,真正有分量的画家,有出息的画家,只有在接近生活中真正有了感受,才能充满信心,主张通过速写“在生活中练基本功,在生活中起草稿”。他重视亲身经历,认为风格是在长期的生活实践、艺术实践和创作实践中形成的。
1975年作 维族歌舞 黄胄对写生的重视来自赵望云的一脉相传。赵望云“农村写生”的观念,在上世纪初曾引起巨大的轰动,为“人生而艺术”“艺术大众化”的主张也直接影响了黄胄的艺术观的形成。 在黄胄的整个艺术历程中,有天才的一面也有苦修的一面。天才的一面体现在他对艺术本能的慧悟。他直接从生活入手,探囊取物般得抓取生活场景中最精彩的一幕,所以看黄胄的画,充满了瞬间的动感和速度。对于大众而言,黄胄的驴子甚至比黄胄更有名,他笔下的驴子憨态可掬栩栩如生,其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精神甚至被黄胄内化而合一。其堂兄梁斌曾经介绍,为了画好驴子,黄胄在新疆下乡时曾经住在“打掌铺”(削蹄钉掌)隔壁,小驴或奋蹄摇尾或喷鼻长啸或倒地翻滚,他都一笔一笔的记下来。只有这种勤奋的积累,才能得生活之真。
1983年作 送粮图 “魔鬼在细节之中”,真实也在细节之中。建国以来“前三十年”的艺术充满了革命激情和政治明喻,思想与思考被压成扁扁的一束,所有的题材模式化,人物模式化,思想和思考也模式化。黄胄之所以能够在其时脱颖,在其后流传,关键在于对生活细节的记录和刻画。黄胄速写所形成的典型的“粗中见精”的绘画风格,其粗见纵横恣肆之势,其精就在于对细节的雕琢。无论是前期的黄泛区的悲悯,还是其后边疆风情的豪迈和欢快,黄胄的感情是自然而然的喷薄而发,他的艺术紧贴民众生活,反映的变化也是平民阶层现实人生的真实细节。
1987年作 驼背上的小学生 通过写生抓取“生活之真”,通过速写将这种细节入画,黄胄通过“写生—速写—创作”的模式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艺术道路。这条道路属于黄胄也属于当代中国画史。从当代中国画的发展来看,50年代黄胄的适时出现,对于解决中国人物画发展过程中“传统笔墨融入造型”“从写生到创作”的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后,传统国画处于徐蒋写实教育体系、延安的革命写实传统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三者的夹缝之中,传统笔墨如何适应时代的需求正成为传统国画家小心翼翼探索的话题,黄胄的速写如同“小李飞刀”,以锐利的姿势打破了种种禁忌,以率真质朴的边疆风情成为各个阶层喜闻乐见的题材,给当时的中国画坛尤其是中国人物的发展带来了一股新风。据中央美院国系教授卢沉后来回忆:“黄胄出来后,大家都很兴奋,原来中国画还可以这么画,松了一口气”。著名艺术评论家郎绍君后来如此评论黄胄速写的时代意义“他用自己的作品表现出画家的天才与勤奋,同时也回答了当时美术界许许多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理论问题。”
1976年作 日夜想念毛主席 黄胄的速写与复笔是创造性的。长期以来,中国人物画局限于元之前的种种描法以及元之后书法用笔,明清几百年的人物画陷入了陈陈相因的萎靡之中。被黄胄引为知己的石涛曾主张“无法而法,乃为至法”“我自用我法”。黄胄以天才恣肆的悟性,以速写求生动,以复笔求形准,以轻舞飞扬的速写和节奏颤动的复笔,“我自有我法”,“我自用我法”,给当代中国人物画的发展在徐蒋之后带来了又一次重大突破。著名画家冯远认为,黄胄一扫明清以降人物画萧索清冷的气氛,一改传统人物画创作中的积习陈规,一破传统国画艺术的章法矩度,代之以鲜明生活的人物形象和富有激情的作品气氛,令当时的人物画坛为之耳目一新。
1981年作 育羔图 黄胄对于当代中国人物画的发展实有开创之功。黄胄从写生入手,以速写入画,得遇名师,成于其时,并影响到随后京派(卢沉,周思聪)、浙派(方增先、周昌谷)、长安派甚至岭南画派人物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此诚是黄胄之幸,也是中国当代画史之幸。
1976年作 飞雪迎春 结识邓拓与苦修传统 黄胄1955年调到北京之后,开始了苦修的过程。所谓苦修一方面是指黄胄为补传统的课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另一方面是黄胄因与邓拓结识所陷入的无妄之灾。邓拓是党内为数不多的有文人风骨的高级知识分子,37岁就担任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五十年代末,因对传统书画的共同爱好与黄胄结为知交,并曾撰文提出了黄胄艺术的著名的三新:人物新,意境新,技法新。邓拓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苏东坡的二副真迹之一《潇湘竹石图》就曾被他慧眼识金而免遭流失海外。邓拓与黄胄交往实为纯粹的文人之交,黄胄因其绘画上的创作力和胆量深被邓拓欣赏。1958年邓拓因“秀才办报”开始被批判,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黄胄就受到了冲击,上万件速写被烧毁,历年珍藏被上交,黄胄也开始了长达6年的劳动改造。
1984年作 众美图 黄胄对传统的认识有一个过程。50年代中期之前,年少成名的黄胄更多的凭的是天分和对生活的领悟,据他自述,少年时代曾觉得传统没什么可学。1955年入京之后,北京丰富的传统资源和深厚的底蕴深深的吸引了他,从此开始痴迷传统,80年代后,他对传统的认识和思考更加深入而深刻,曾有一方印“黄胄晨课”,专门加盖在清晨的临摹作品上。黄胄对传统研究和认识有自己辩证的观点,在一幅题记上写到:“前人之法不可不知,不可不用,不可不通,但不可生搬硬套”。黄胄学传统但不泥古,如写生一样,黄胄对传统的研究强调的是为我所用,所有的技法不内化不“笔墨当随时代”都是刻舟求剑南辕北辙。
1981年作 欢腾的草原 这种辩证的思路让黄胄对传统的认识在五六十年代有了快速的提高,很快他就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收藏家,和邓拓的交往也扩张了这个圈子,包括与徐邦达、张葱玉、刘九庵等著名鉴定家的交往也逐渐频繁。据当年宝古斋当年的经理陈岩在《往事丹青》记述,在此期间,黄胄凭借自己的悟性获得了不少国宝级藏品,比如元代张师夔、雪界翁合作的《松鹰图》、明代边景昭的《双鹤图》,以及明代陈洪绶的《麻姑献寿图》等。 对于在中国画上的成才,黄胄显然是个异数。他是先凭天份,后修传统,得力于较少的框框约束,他创造出了速写入画的气势风格,有力的补充了中国传统绘画教学的不足,得力于苦修传统,他的绘画愈老愈精,1984年的《雄鹰图》很明显看到他对传统的回归以及对传统的改造。对于黄胄而言,结识邓拓扩大了他对传统研修的圈子,但也带了随后的艰苦岁月,幸或不幸,也都是那个时代所赐。
1982年作 草原追嬉 黄胄与新疆 从黄胄的一生来看,黄胄实际上是个综合型画家。其师赵望云倡导农村写生,但更多的还是以山水为主,黄胄则是人物、动物、花鸟均有涉猎。黄胄的题材广泛,维族、藏民、内蒙、黎族、白族、海南渔民都是他绘画的重要题材,晚年还欲以黄山为师,可惜时不待我。 但从作品的题材构成和重要性而言,新疆无疑是黄胄的福地,几乎所有经典的作品都出自新疆,无论前期的《洪荒风雪》《庆丰收》《载歌行》还是后期的《姑娘追》《叼养图》,无疑都是得到了新疆风情和维族风俗的深厚滋养,说新疆成就了黄胄毫不过分。黄胄是社会风情的记录大师,他对新疆风情和风俗的理解是刻在骨子里的,他所有的细节描摹都准确无二,而新疆的姑娘、边疆的骏马也成就了黄胄。速写优势所体现的速度、动感和线条的韵律,也只有在西北草原的天高云淡和风驰电掣里才能找到最佳的表达,仔细研究黄胄的作品,你会发现在其他的地方的题材中,速写的这种技法的优势,会大打折扣。
作品 赶集 诸多论家对黄胄的研究都集中在写生与速写上,这种群体偏好忽略了新疆风情带给黄胄的另外一种滋养—黄胄绘画中色与墨的融合。在中国传统文人绘画中,由于对水墨的热衷和文人趣味,画家和藏家对色的排斥都到了极端的地步,色与墨的融合到了近代才有三次突破。一次是以赵之谦和吴昌硕为代表的海上画派,为适应新兴商业市民阶层对吉祥如意的偏好,发展了红色入墨的海派传统,这种风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被认可,尤其是在上世纪初北京的文人圈子,描述一个人画的“海”,是表达对“俗”无限的不屑。世变时移,什么都敌不过间,后来被齐白石发展成“红花墨叶”的传统格式,最终也成了经典;再一次的色墨融合的突破,也发生在大西北,以石鲁为代表的长安画派用红褐墨三种颜色,交叉描绘西北黄土的苍黄与厚重,这种色墨的融合只有在描绘西北黄土高原的时候,你才会不觉的突兀,不觉的“脏”,觉得自然而言;同为长安画派传承的黄胄把这种色墨融合的感觉成功地转移到了西北维族人物上,他们的艳丽多姿,他们的激情活力,让黄胄把色墨融合运用的炉火纯青,这种色上加墨,墨上加色的模式,也只有在这种激情的宣泄中,才会有如此不羁的表达。关于此点,笔者才拙,希望更多的论者予以研究和关注。
赶驴图 中国画研究院和炎黄艺术馆 即使在现在,位于紫竹院的中国画研究院(现为国家画院)和位于亚运村的炎黄艺术馆,也是北京人眼中著名的两个文化地标。但就是这两个建筑几乎耗尽了老黄胄晚年所有心血,中国画研究院黄胄败走麦城,蒙冤受屈至今未见昭昭天日般的洗清,其后的炎黄艺术馆则是黄胄心胸和视野的体现,几乎成了他纪念碑式的作品和存在。
美术馆和博物馆的兴起,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艺术现代化的标志。近代文化先驱蔡元培、胡适都曾有过热切的设想,近代美术两位奠基人林风眠和徐悲鸿都曾不止一次的呼吁过 ,徐悲鸿曾言:“国家唯一奖励美术之道,乃在设立美术馆”,“现代之作家,国家诚无闲一一维持其生活。但其作品,乃代表一时代精神,或申诉人民痛苦,或传写历史光荣,国家苟不够致之,不特一国之文化一部分将付阙如,即不世出之天才,亦将终致湮灭。其损失不可计偿。”其言凿凿,其心切切,惜其早逝,终无结局。在近现代画家中,有美术馆的意识、有不顾一切的勇气和胆量,有“必攻不守”执行力的,唯黄胄一人而已。
做为民办公助模式的第一家艺术馆,炎黄艺术馆承载了太多,也经历了太多,令人欣慰的是,他体现了黄胄“必攻不守”的精神,践行了赵望云“艺术大众化”的主张。炎黄艺术馆从开馆以来,严格的学术体系和学术展览,至今泽被热爱艺术的大众,成为大众艺术教育的典范。 大家和大师是后人对先贤的两种评价。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大家有时代感,而大师有历史感。大家肩负着时代担当,大师则背负历史责任。黄胄的艺术成就足以成为他那个时代大家。偶看文章,有论者论及黄胄艺术成就和地位说,大家距离大师只有一步之遥。笔者才拙,窃认为,对于黄胄而言,有了炎黄艺术馆这个丰碑,这一步足以补上了。黄胄是这个时代的艺术大师,是无疑的。 |
 腾讯微博
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
新浪微博 网站地图
网站地图 手机站
手机站